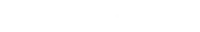这馄饨馅是馄饨的灵魂,肉、葱、姜等调料按一定比例调制,肉必须用前臀肩,七分瘦三分肥,要把馅经过无数次的搅动,直到馅十分均匀才行 。因为皮薄,馅的颜色从外面很容易看出,红里透白、白里透红,从视觉便可产生美感,也就更增强食欲 。
下面咱们说说这非常讲究的馄饨的汤,汤的内容可相当丰富,不光有猪棒骨,还要放上两只鸡,您说那汤的味道能不地道吗?盛馄饨时,碗里再放上蝦皮、 冬菜、紫菜、香菜、酱油、味精、胡椒粉、醋、辣椒,等喝馄饨的时候,您再配上烧饼,嘿~保您吃个满意!

文章插图
还有必须提的是我父亲头脑灵活、敢想敢干 。以前买卖小的时候只卖馄飩和芝麻烧饼,资金稍可周转之后,就开始卖熟食和小菜儿了 。后来有了啤酒(啤酒桶像个煤气罐儿,里面装啤酒,一根铁管插到桶里,上面像水龙头节门一样,卖一杯,放一杯)这在当时,也是从我家开始的 。后来在我家旁边增加一家卖褡裢火烧的刘三大爷,品种更多了,也算优势互补 。再有就是招牌,自己宣传自己,我曾清楚的记得,父亲摊位的后墙上,挂着一个帐子,帐子的底色是紫色,上面书写“馄饨侯”(仿宋体大字)和“北京风味”(仿宋体小字)周围是一圈和平鸽(当时正值抗美援朝)装饰,其实就是一圈馄饨吧!
当时京城诸多媒体对我家“馄饨侯”都有着详细的报道 。例如:《旅行家》杂志(1957年4月号)41页,金受申先生撰写的《北京的夜》一文中,由毓继明先生画的钢笔速写插图,画面的前景一排人坐在木凳上吃馄饨,后景布棚内挂一布帐,帐上写着“馄饨侯”三个大字 。《北京游览手册》(1957年版)136页第10行写到,“馄饨”北京馄饨铺和馄饨摊很多,东安门东口路北“馄饨侯”较有名(晚间营业) 。《国际畫报》1956年版刊登了背景是“馄饨侯”横幅的,父亲和大妹的照片 。

文章插图
在这期间“馄饨侯”的名声越来越大,成为了京城响当当的餐饮品牌 。
由于大势所趋,1957年的合作化,公私合营,我家的买卖也发生了变化 。当时在东安门一带经营馄饨摊的有很多家,因父亲名气较大,人又正直,很有号召力,被大家选为组长,地点指定在南河沿东皇城根南口,但这个地理位置显然无法和原东安门(现改为东华门)靠近王府井的街面相比,顾客寮寮无几,加上合作化,心气儿也不高,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,众人十分着急,想重新回到东安门的街面上经营,但再以“摊儿”的形式出现是不允许的,只能以“铺面房”的形式回归东安门大街 。
经过考察后,选定东安门原“馄饨侯”附近的铺面房,1959年迁入新址经营 。因为合作前摊商“馄饨侯”早已为人们熟知,上级部门也认为这个名字好,因此沿用了“馄饨侯”的名号,沿用至今 。父亲任经理,一直到文革初期,在这十多年里父亲作为经理,为“馄饨侯”的发展壮大作过极大的贡献 。以下几件事是值得提起的
1960年11月的一天,突然上级领导通知父亲带好厨具去人民大会堂,到后才得知,周总理请缅甸总理吴努品尝北京风味小吃,是周总理亲自点名要我父亲前来 *** 馄饨,款待客人的,此后父亲曾数次去西颐***献技 。在父亲的培养下,他的徒弟在六十年代初参加全国烹饪比赛得了金奖 。
美好的时光飞逝,文革开始了,作为北京的“名人”父亲遭受了批斗、游街、受尽非人的虐待,难道这一切都源于小小的“馄饨”吗?
文革期间我们六个子女中有五个因分配,下乡插队离开北京,父母亲不光要遭受身体上折磨、精神上的摧残,连孩子们也被迫离他而去!这时父亲的病越来越重,因为得不到医治导致失语,但扔要上班 。
由于残酷的批斗致使他在1973年病情更加恶化,导致半身不遂 。在母亲和弟弟、妹妹的精心护理下,病卧八年 。1980年10月30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。

文章插图
为什么我们兄弟姐妹没有继承父亲一手创下的“馄饨侯”?现在回想起来才终于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。按道理家中兄妹六人,我这个老大应该替父母分担一些压力,但在1958年我初中毕业时父亲坚持要我考高中(文革时这也是他的一条罪状),父亲供我上学这个事,在他周围是不多见的,父亲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,不希望我们再去受他那样的罪 。1961年高中毕业后,我考上北京钢铁学院,1966年毕业后,一直从事教育工作,2002年从黄金系统的一个学校退休,职称是高级讲师,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,为了我们吃了那么多苦,把我培养成一名高级讲师 。
推荐阅读
- 海拉尔区融富馄饨馆_工商信用信息_经营范围期限状态_法人_地址_注册资本_怎么样
- 怎么做白菜馄饨 白菜馄饨的做法
- 馄饨怎么包简单的方式 包馄饨的方法介绍
- 侯嬴怎么读 侯嬴的读音
- 馄饨的煮法 馄饨怎么做
- 士死了叫什么 诸侯死了叫什么
- 因九合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是什么
- 苏轼留侯论原文翻译与阅读训练 关于文言文留侯论原文翻译
- 航海王燃烧意志侯斯怎么打 通关攻略分享
- 4月15日起 闽侯县解除封控管控管理